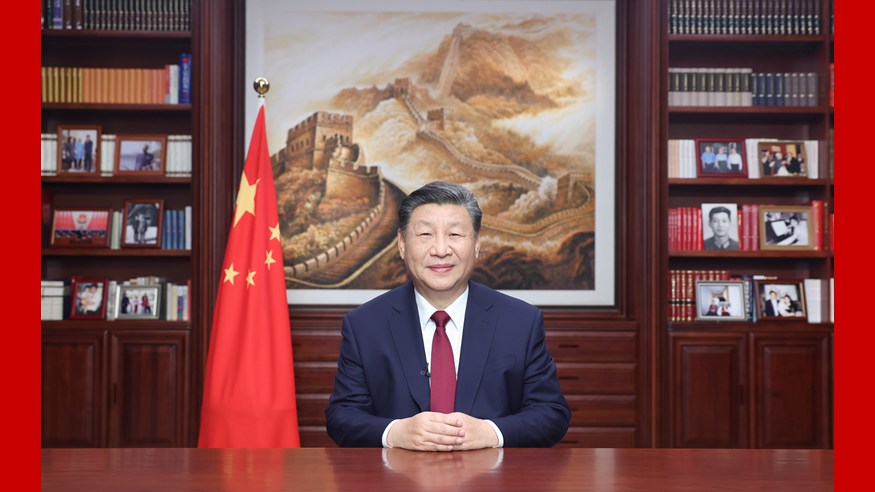理钊离开我们已经两个多月了。至今我还是不肯相信,因为时常觉得他还在,就在周围忙碌着。他那宽厚的性格,儒雅的风度,他的勤奋与才华,说话时的轻松和幽默,还有他的堪称尊贵的文化情怀和不曾放弃的社会责任心,一直都在我眼前跳跃着、连续着,如同一个个视频小品。如果将这些连接起来看,我发现,在这里,在我心中,没谁能替代他。
那是三月二十一日晚上,书院副院长杜振北先生三打电话说,理钊可能出什么事了。他是从一位诗人刚发在网上的一首诗里看到的,口气惶惶,但消息尚未最后落实。我当时猜了几种情况,都不是。振北说,那首诗中的句子有不祥之语,好像是人走了。我感到一阵不可名状的震撼——怎么会呢——可是没谁会拿一个人的生命恶作剧啊。他说继续落实。很快,消息成为噩耗——就是那天下午五点,理钊突发心脏病,不治而去……
晴天霹雳,五雷轰顶,这些词语都无法描述我当时的感受!无论如何我都不肯相信他会突然离开我们。理钊是我多年的朋友,而且是志同道合的挚友,彼此相知,十分默契。我还有很多话要和他说,还有很多事情要依赖他,临沂不能少了这样一位才人、好人、君子。2019年的这一消息对我的打击如此沉重,以至于无法入眠!理钊不仅是我个人的朋友,他也是当代最真诚的富于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一位杰出的文学评论家。有他和没他,对于中国杂文界是很不同的。他这样的人走了,杂文领域有好大一片将变得荒凉!这噩耗如此突然,如此生硬,生生逼人接受——真是人生无常啊!
去年秋天,理钊有过一次类似中风的经历。当时的情况,据他自己说,那只是几个小时的失忆。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希望认真检查一次,找到“失忆”的病理根据。我郑重提醒他,那很可能是心脑血管的问题,是中风的前兆。他不肯相信,以为只是疲劳引起的瞬间昏厥。我宁肯如其所述,但我的亲友中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说心脑血管疾病的初期征兆就是这样的——不免暗自为他忧心。去年年底回京前我曾对他说:天气渐冷,出外最好戴个帽子,以免头部受凉。他满不在乎地说:“习惯了不戴帽子——你放心,没那么严重。”
然而,第二次发生,竟然要了他的命!
谁能想到?
近年来,有两件事让我感到巨大的伤痛,一件是母亲的去世,再就是这次理钊的离去。母亲的去世给我带来的悲伤是因了血缘,那是人人共有的。但母子间的感情更多地出于养育之恩,从思想层面上说,理钊的离去给我的伤痛远大于母子永别,原因是我和他有着全面而深入的精神交流。他是我志同道合且情趣相投的兄弟,几乎在每件事上我们都有相同的认知,而且朝着同一目标努力。另一不同是:母亲离去时已年过耄耋,而理钊才55岁!这不应当是他的生命的终点,不应当就这么走了啊!他还年轻,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且他也具备做好那些事情的能力和智慧。如果有上帝,上帝经常是不通情理的,它将爱情中的年轻人赶出了伊甸园,将才情丰茂的理钊过早带走——真应了天妒英才那句话!
人生是一次旅行,古人称之为逆旅,逆向之旅。人在这个旅途上偶尔遇到一位相知,是一种莫大的幸运。我的一生,一半像是逃离,一半像是寻找。逃离农村而后逃避城市,逃离传统而后逃离现代,逃离孤独然后逃离热闹,这一切似乎都是为了寻找几个朋友。我找到了一些,不多,这些朋友当中很重要的一位就是理钊(他多次要求我直呼其名)。我曾经追问:为什么是这些人而不是另外一些人?答案是:一个人的内心终究还得靠了解你的人去评判,只有这些人才可能成为好友,领导的意见,群众的评论,亲疏的褒贬,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识者之见。朋友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因世事变迁而中途失散的,因意见相左而分道扬镳的,因趣味不同而若即若离的,远远多于始终如一的。我和理钊都反对依附和迁就,都反对愚忠和乡愿,都反对趾高气扬或自甘卑下。也许因此,我们才成了朋友。
我第一次见到理钊,是在沂河宾馆。那个老宾馆后来因建在河道的行洪区而被拆了。当时他和诗人张斌一起来看我,我们谈得很投机。后来我每次到临沂,都会争取和他们见面聊聊,渐渐就有了认识。
理钊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忧时伤世,赤子之心拳拳,却不曾有过颓废和放弃,犹如鲁迅先生所赞扬的韧斗。他渴望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渴望人和人之间平等对话,彼此守着信用和契约,绝不做损人利己的事。他向往民主和自由,赞赏美好的人性和品德,也深知友谊和感情的分量。他对一切危害社会的特权、腐败、傲慢和愚昧痛心疾首,即使面对不公正的对待,他也不曾屈服,字里行间一直洋溢着追求真理的勇敢和坚毅,如同堑壕里的一名狙击手。从这一点上说,他是这个时代的堂吉诃德,正是这种“不自量力”的一根筋精神,体现了理钊一生最为核心的价值。
理钊毕生都在追寻先进文化,孜孜不倦,坚守着科学和理性的方法论,比如笛卡尔的怀疑论,孔德的实证论,还有近当代学者所崇尚的严谨的逻辑。和欧洲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一样,理钊高度赞赏独立思考,反对人云亦云。东夷书院近两年的课程是他安排的,其中周文臣先生关于启蒙时期的哲学和理钊关于洛克和《政府论》,是2018年的重头戏。为了讲好这一课程,他们读了大量汉译名著,而且做了详细的课件,讲课效果很好。此前,理钊还对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做了当代视角下的解读,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本来,今年的课程打算由他讲解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可惜,我们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他再也不会登上书院的讲台,我们再也不能分享他的思想成果了。如今想起理钊当时讲课的情形,眼前就会浮现出他那挚爱先进文化的执着,让人感叹这位堪称凤毛麟角的人物给书院带来多少精神财富!一棵大树存在的时候,人们感觉不到它的恩惠,一旦它倒下,大家才会感受到那种莫名的失落和难言的悲伤!
理钊对文学情有独钟,终生沉浸在阅读和评论的乐趣中。他不仅读了大量小说、散文、诗歌,还写了海量的杂文和评论。没写过评论的人可能不大清楚一篇文章的形成需要付出多少精力。假如是一部三十万字的小说,仔细读完,大约要一周的时间。如要写评论,还得精读细读,将重要的章节和句子记下,把对人物、主题、细节的各种感受仔细梳理并和古往今来的同类作品加以比较,然后构思框架,琢磨表达方式,形成草稿。放些时日,再拿出来修改(有时是多次修改),才能成为一篇文章。读书和评论不仅需要思想的高度,精美的文字,也需要体力!为此,理钊付出了不知多少心力和体力,熬了不知多少个夜晚,这一定损害了他的健康。我想,所有曾经被他评论过的作者都会为此而伤悲,为此而揪心。
评论是一把双刃剑:评论写得精准而深刻,言别人所未言,大家都说好。一旦说过了,说低了,说漏了,不是作者不满意就是读者有看法,受伤害的往往正是那个写评论的人。还有一层无关文字的难处:评论这个没评论那个(或尚未来得及评论),也会引起误会——我的作品怎么没入你的法眼啊!实际上不是这回事,因为理解一个人的某部作品,需要很长的过程。我曾和理钊讨论过这类事,他最感苦恼的是“不能批评”,不仅社会不能批评,各种作品也都不能触及缺点——只能说瓜甜不能说瓜苦——而这正是批评的要害和灵魂。假如有个完全畅所欲言的人文环境,理钊的心情会更好些,写出来的文字也会更有看头。其间苦衷,确非三言两语所能及。
理钊是一位思想敏锐、文笔犀利的杂文家。他对社会弊端和文化积垢的批判足以被称为一位文化的清道夫。在铺天盖地赞美皇帝的黑潮中,他以学者的严谨态度分析了康雍乾时期的黑暗、极权和傲慢,撕破了一帮无聊文人编制的所谓盛世。同时,他的批判锋芒也指向人们司空见惯的各种恶习,如依附性人格和奴性,如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如道德的无底线等等。理钊去世前还对羽戈的一篇讨论戊戌变法的文章给予了充分肯定,我们就此讨论了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变法失败后清廷却吸收了变法中提及的各种纲领(如废除科举等),为什么君主立宪没有成功,假如张之洞或别的人操作此事会是怎样的效果,等等。
理钊的文化价值很大程度表现在他的杂文上。就思想的高度和行文风格,理钊的杂文已不单属于临沂,他是全国层面的杂文家。从近年来发表的杂文看,理钊具备了一流杂文家的思想水平,也拥有一流杂文家的文采。假如老天再给他20年时间,理钊将成为中国杂文界的最高层次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就我们的生存环境,就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来看,理钊的杂文具有深厚的内涵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许多作品脍炙人口。可惜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杂文家,这是永远的遗憾。近几天,很多中国著名杂文家都对理钊的离世表示了痛惜之情,就是证明。这样的作家不是三五年就能培养出来的。黑夜给了他明亮的眼睛,老天爷让我们眼看着这双眼睛消失在一片暮霭之中。我相信,只要还有腐朽,还有黑暗,理钊的眼睛是不会闭上的。他在天堂看着我们,叫我们不要松懈,不要妥协,不要自甘平庸。
批判的同时,理钊也肯定现实的每一次进步,对真正趋于文明的事物不吝歌颂。他一直强调财产不能共有和权力不能私有,这方面,中国的民营企业促成了社会的进步。不久前,他还对有人宣扬“国进民退”的说法深表担忧。后来中央发表了一连串的消息并制定了保护小微企业和切实的减税政策,理钊感到一丝欣慰。山东官本位意识很重,理钊相信去掉官本位不能靠口头上说,八十年代的分田到户和九十年代的下海经商才是消减官本位的核心力量。他赞成社会的多元化,而这种新思潮的形成不仅是大势所趋,也将伴随着世界的共同进步而显示出光明的前景。相对于那些喜欢把希望寄托在个别人的开明之上的颟顸,理钊更相信制度的力量、科学方法的力量、觉醒者的力量。
理钊离去的这么早,和他长期大量阅读和勤奋写作不无关系,也还他的君子之忧有关。他的阅读和写作是很用心的,心力的透支是对健康的伤害。体力劳动,只要不过度,不仅能促进新陈代谢,还能锻炼身心。写作则不同,在最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却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在最需要强健身体的时候却不断销蚀着既有储存。长期熬夜,过度用心,让死神窥见了可乘之机。理钊不是不知道这些道理,他总是面不辞人,或者说,他有一种提携青年,扶持新进的责任感。临沂作家,包括我,都曾得到理钊的关注,都曾有幸得到他的评论。他用自己的劳动为文学和一切热爱文学的人亮了一盏盏路灯,而他却过早地走了。
理钊也是一位孝子,一位自认为对家庭富有主体责任的人。父母多病,他侍候的最多,几乎每天都要回家看望父母(这也是他父母的渴望),全家的周末聚会几乎都是由他操持饭食。理钊的整个家族很团结,这和他这个长子的不辞辛劳分不开。侍候老人是一件非常辛苦且没有乐趣的事,理钊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在单位,他是领导倚重的人,重要文稿几乎都要他的订正和润色。理钊对于文字十分认真,从来不肯敷衍。在他的行文中,几乎看不到因为电脑打字造成的错别字。他喜欢把文字先手写下来,然后输入电脑,这也加重了写作的心力负担。
我和理钊,在创建东夷书院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感情交流。在明白我建立民间书院的意图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建立书院这件事,就社会功德来说,可能胜过你写的所有小说”。这句话对我是极大的鼓励,也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发自肺腑的声音。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能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理解历史、文学和社会。此后,他们夫妇经常参与书院的活动,理钊成为书院的主要讲师,他的夫人对书院同样也是关怀备至。他们真爱书院,将书院视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在担任书院教务长后,理钊不仅负责课程的安排,还热情延揽了许多优秀学者参与讲座,包括引荐周文臣先生。他们的参与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也让书院的课程更加丰富也更有深度。理钊经常担任讲座的主持人,他总能准确的概括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给同学们明晰的理解经纬,因此成为大家依赖的先生。2019年的课程,他已安排好了,可是,课程尚未开端,他就走了。他要讲的课已经落空,让我因此产生了老天要亡我书院的不祥之感。不然,为什么生生摧毁我们的台柱,为什么夺走了我们心爱的教务长呢?
理钊的短短一生,让我们看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贵精神,让我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正能量,看到了草根间蕴含的文明力量。理钊虽然身在体制内,但他没有官员的傲慢和保守,总是那么积极乐观,对未来充满信心。他活跃在文学艺术园地里,但没有文人的迂腐和清高。他总是兴趣盎然地对待生活,从来没见他有游戏人生的风尘气,也没有无病呻吟的小情小趣。在博学和实证方面,他条分缕析,类似胡适;在批判和分析方面,他思深虑远,文笔犀利,有人称之为临沂的鲁迅。他谨言慎行,处事有分寸,富有幽默感,这一点有点像林纾。他孝敬父母,忠于朋友,不辞家务琐事,这无疑来自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是其个人品性的表现。他读了很多书,但从不自诩,始终保持着谦和的态度和凌厉的批判精神。他从不讨好,也未曾屈服。他的精神背影和西方启蒙时期那些伟大知识分子有着某种重合,也和中国古代那些富于忧患意识的文人相似。理钊是当代中国拥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优秀的士。
他有他的无奈,那不是他一个人的感受。在个人无能力为的时空,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和责任。他给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当一个看客”。其实,他不是一位旁观者,应当出手的地方,他总是当仁不让,从未畏缩。他视野宽广,密切注视着中国和世界的变化,随时提醒自己应当做什么。在不属于书生责任的地方,他也寄托着热诚的希望。理钊是一位很全面的文化人,很难有人填补他的离去所形成的空白。有人比他读书更多,但像他那种拥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那种关心社会的家国情怀,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具备就能拥有的。我当然希望有人尽快填补理钊留下的空白,希望家乡出现一批理钊式的才人和贤人。惟其如此,这个社会才会有健康的未来,才会有进步和文明的生气。
最后一次见面,是2018年12月的一个雪天。书院的几位主事的同仁说,找个机会,最好是下雪的日子,去书院那边烤火喝茶,总结一下书院当年的工作并制定下一年的计划。我当时正准备去兰溪参加《芥子园画谱》的学术研究会,打算回来就聚会。我开玩笑说预感到那天要下大雪,老天可能要给我们的雅集一个美好的情境。果不其然,聚会头一天晚上,临沂真的下了雪,而且很大。次日一早,理钊夫妇先来了。屋子里太凉,我和理钊负责生火,打算先把炕烧热,让室内温度升高一些。理钊拿了砍刀,在院子里劈柴。他把柴火分成三个部分,最细小的用来引火,然后添上中等的,等火旺起来再填上较大的木头。看他劈柴、烧炕的样子,不熟悉的人真想不到他就是那位写出那么多脍炙人口评论的文章圣手。老天爷如此无情,它总是将那些练达、睿智、富有正义感的生命强行夺走,而让行尸走肉遍地开花。

那次聚会,大家很高兴,理钊也喝了一些酒。高兴起来,说到各类文化娱乐活动,理钊说他曾是一位音乐发烧友,古今中外的唱片听了不少,收藏甚丰。后来他又喜欢上电影,在家里做了个小影院。我说我楼上有两间房子空着,也想做个家庭影院。他向我介绍了做家庭影院的一些知识,重点是音响,还要做好暗室效果,窗帘和吸音设施都要研究,一组上好的音箱要花很多钱,等等。他说他的一位朋友是搞这个的,等我下次回来(就是这次),请他给设计一下。我很高兴,一起做了预算和计划。有个好的放映室,同学们看电影就方便了,因为接下来要讲的有关外国文学的课程是要看几部电影的,如《安娜卡列尼娜》、《巴黎圣母院》、《飘》……
就在他离去的前几天,我们还商量了请北京几位学者来书院讲课的事呢。兼收并蓄,各抒己见,自由讨论,不求一致,是书院讲座的宗旨。我们请的学者中既有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崇尚现代文明的自由主义者,既有体制内的,也有民间文化的传播者。这一点,得到理钊和全体书院同仁的赞同。书院有三不讲:不讲当代政治,不讲宗教课题,不谈性爱话题。这三不讲,有很多人误解,以为我们是文化的侏儒,是胆小鬼。不是这样的。因为:从科学意义上讲,以上三个课题,都需要两方面的支撑,一是详细占有被证实的资料,一是研究者应具有独立思考的理性和能力。这两方面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妄谈瞎扯,只能是盲人瞎马夜半深池。因此,在不可能充分占有可靠资料的情况下,只有先行完善我们的主体能力,即思想的方法和分析的理性原则。基于这种思路,我们尽量避开现实话题,集中力量做些认识论上的功夫。理钊留下的“作个看客”的遗言是他离开人世前留给我的告诫。说完这句话,他就走了。这给我无限的痛苦。不是说好一起当个看客嘛,你怎么就走了?从此之后,我将独自看着眼前的一切,再不能和你一起讨论,再也没有你给我的“另一视角”,也不会再有你的旁征博引,我还有什么心劲看下去呢!有那个必要吗?我已是这样的年纪,天塌地陷,与我何干!没法写下去了。
理钊,还有他夫人卫华,给予我们的不仅是一份朋友的热情和信赖,还有生活的立体感和精神上的亲切感。每当想到理钊夫妇,想到书院有关的那些朋友们,我就觉得临沂还有个家。理钊作为这个家的灵魂人物之一,走了,因此让我觉得而这个“家”面临着破败的前景。我知道,理钊一定不赞成我的这一想法,他在天堂向我们招手:好好做下去,不要因为我的离去而颓废,我在天堂那边继续为书院祈福呢……善良而真诚的他,一定会这么说的。夫复何言!
王兆军简介
王兆军,著名作家、学者,临沂河东人,复旦大学文学学士,著作丰富,兼长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古体诗,多次获中外文学大奖。近年新作主要有《书圣之道——王羲之传》,长篇纪实文学《问故乡》及《黑墩屯》、《朱陈》村史。2016年,王兆军出版《春秋故城祝丘》和《乱世之花-文姜传》等。2015年,王兆军在临沂河东区凤凰岭创办东夷书院。《新华每日电讯报》曾以《回乡办书院——一位作家的支农心得》为题专题报道东夷书院。书院教材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品味古籍”专栏连载。2018年,王兆军与同仁在微信平台推出“百人计划”,瞩目临沂人的生存境况和文化进步,目前已刊登30多篇人物特写,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
王兆军钟情山水画,尤擅焦墨。他的焦墨画得益于雄厚扎实的文学修养和对艺术的精到理解。王兆军的山水画师承黄宾虹、张仃等大家,其作品浑厚苍茫,气韵生动,品位高尚,独具一格,为国内最优秀的焦墨画家之一。2018年10月,临沂美术馆举办《王兆军文学艺术作品展》,引起普遍注意和一致好评。